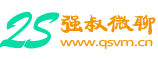在岛屿之间
文:陸俊文-Perry
从公寓走往图书馆的路上,我常能看到那些白衣黑带的修女,她们平和优雅的面容总让想起在厦大校园里漫步的南普陀和尚。
刚来台湾的时候冬天还没有过去,转眼现在已经入了夏。学校建在台中近郊的大肚山麓,纬度正好和厦门岛平行。三月底南投地震,我在床上沉睡被摇醒,隔海相望厦门的同学说他们也晃荡了一阵。总归是一衣带水,不止是忽冷忽热的气候相似,连昼夜不停的风也一样有劲。
由于天主教会学校和原先女校的缘故,这里显得过分的安静。习惯了在厦大看每天来来往往的游人,对这里一到周末便人去楼空的校园并不大适应。所以除了躲进图书馆看书,便是到附近镇上沾沾人气儿。
沙鹿镇上的早市很热闹。我曾在一个周日的清晨把两个朋友送上去台北的火车,因为路况不熟,只得询问路人,偏偏答我的婆婆不通晓国语,她提着菜篮子手脚并用,一口断断续续的台语,指着对面的路,七拐八弯的比划,我只得不停地点头又摇头,于是拖着行李箱穿进了热闹的集市里。要赶火车,却又卡在了这难以前进后退的人流中。原本冷清的街道在这时候摆满了密密麻麻的果蔬摊点。我一边抱怨着,却一边看到了穿着缀花薄衫的阿妈们心满意足地抱着大颗的菠萝。这熟悉的市井味道,仿佛是从鹭岛厦禾路的街摊蔓延而来,缠绵着咸咸海风,还有浓浓的人情。
只可惜鹭岛一年四季从各地涌上岸的游人太多了,拥挤到都没有自己的藏身之地;而沙鹿这里,公路上看过去都是清清静静,一路延伸着通往山道,两旁参差的独栋小楼,常让我想起日本电影里小镇的图景。
我住的公寓是可以看到海的。从走廊或是阳台探出头去便是整个台中市景,沿着边同蓝天过渡的部分便是海,西海岸的水没有东海岸那么汹涌澎湃,总带点郁郁寡欢的柔情,又常常同天色一道暗下来。太远了,也只能目触些模糊的痕迹。
对台中市的印象长久的停留在了绿园道。那天晚上和三个朋友从广三SOGO出来,要去附近的诚品书店,路上却被街头唱歌的艺人吸引住了。一个吹萨克斯,一个弹着电子琴演唱,两个人看上去至少都有三四十岁的年纪了,可他们却分明笑得那么开心。他们就站在一条公路边缘的一棵大树下,身后是奔驰着飞过去的汽车,眼前是围了好几圈驻足聆听的市民。有年轻的刚吵架又和好的情侣,有推着婴儿车出来散步纳凉的年轻母亲,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刚下班还穿着一身正装的白领。我们坐在一条水泥砌的长砖上,才坐下去他就开始唱王菲的那首《人间》。惊讶于他那温柔细腻的嗓音,虽不似王菲那般轻盈空灵,却把这“人间”唱得如此真挚而沧桑动情。那天晚上稀疏的叶间落下零星的雨滴,风扑面而来,我们就这么长久地坐在那里听他们的唱和与吹奏,直到十点整,他们的时间到了,人群要散了,我们才迟疑地挪动脚步离去。
原本以为市区里的人都朝九晚五、忙于奔波,难得闲情停下来,可没想到音乐是那么轻易地就把人聚拢在一起。那一刻我觉得那两个沉醉地吹着萨克斯和入情地抚琴而鸣的老男孩和诗人那么的相像,站在那里,就有足以打动人心的力量。
对一座城市的喜爱常常就在这样的不经意里。就像想起花莲会想起那个和当地人一起在南滨公园边打沙滩排球的夜晚,想起绿岛就会想起望海轩老板嚼着槟榔和我们调侃时的笑语,想起垦丁就会想起在庭院里饮着梅子酒和友人把酒言欢的那份闲情。而台中绿园道唱歌的街头艺人,成为了我每次站在公寓眺望,都会想起的场景。
其实在厦大白城沙滩上也常常会有一个夜里在海风中吹着萨克斯的年轻人,我看见过他好几回,有时候涨潮海浪漫上来了,周围已经寥落无人,而他仍在独自对着海独奏。孤独的背影和曲调不得不让我想起费里尼《大路》里的小号、杰索米娜的笑。有些人总是那么执着地去追逐一样东西,十年二十年甚至一辈子;而我们大多数人,总是在跨出去一小步的时候就哆哆嗦嗦把脚从满布荆棘的小道上收回来踏在平稳的土地上吧。
时间是个太过迷人的东西,却也是个太懂得催人泪下的药剂。
想起在杭州的时候,爬宝石山,下来在半山腰路遇一家叫“纯真年代”的书吧,隐蔽在丛林之中,轻掀珠帘进去,为里面沉静安逸的阅读气氛所吸引,随手把书架上的书翻开,封页间留有作者馈赠的笔迹。事后得知书吧的主人竟是一对爱文学的夫妻,还都是厦大的校友,妻子读外文系,丈夫读中文系。想想更惊呼,几年前所读到,林丹娅老师在散文中提到的那对在西子湖畔开书吧的神仙眷侣,她的那个朋友,不正是这间书吧的主人吗?因为十年前的一场重病,在迷离边缘的她毅然在西湖边开一家书吧,而她丈夫也倾其所有为她开店。之后她病愈,辞掉了高校的工作,专心打理这家书吧,成了远近文人名士流连的一方小天地。十年,书吧从西湖边迁到了宝石山上,每年都在负债亏损,可他们仍旧坚持着,开文学沙龙,办书吧活动。
若不是真的踏进去,我还不肯相信这如小说情节的故事竟是真事。念想着人生是个多奇妙的东西,若非在紧要关头,或许先前的迟疑不定断然不会如此决绝,而经历了多少年岁多少事,依旧惦记着那份“纯真年代”,又是多么的难能可贵。佛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才会有那么多意料不到的偶遇吧。
三月底,两个朋友从大陆到台北来,要我给他们找住处。因为行程决定得匆忙,我几乎把全台北民宿和酒店的电话都拨过去了,一一回复我客满。在晚上几乎要放弃的时候,却不经意在阳明山上一家民宿那里订到了空房。朋友事后告诉我,那家店太特别了,每天都只在晚上才挂出自己的信息,白天就关闭。这的确太过有缘。主人也是一对夫妻,丈夫是园艺师,亦作建筑设计,朋友在阳明山上住的那栋日式别墅便是出自他之手,妻子是个画家,也种花,他们结婚已经有几十年了,从中学时候相恋到现在,感情仍是如此甜蜜。朋友告诉我说房间、走廊里摆满了他们的雕塑和画作,其中有一幅很别致,是丈夫还在读中学的时候就画给现在妻子的油画,框在那,钉墙上,仿若时间的游弋,几十年就那么呼啸过去,画中人已老去可笔落处渗出的情意却浓得像阳明山上的雾气风吹不散雨洗不淡。
朋友还反复同我提及主人在庭院里种的花,提及这庭院静谧得仿若云深不知处的仙境。那些东西可以离你那么远却又可以离你很近。
我记起自己之前在漳州,常常看着隔海相望的厦门岛,于是就索性坐船过来了,等天黑了再又乘船而反;之后住在厦门,东岸边每次雾散去看到金门岛又总是惊呼不已。而如今在台湾岛回望大陆,我确定它就在我望去的方向,很明确地存在那里,闭上眼,形状模样如此清晰,可睁开眼使劲张望,却只见白茫一片。
忽然发觉其实身处哪座城市哪个岛屿最打动我,并留存于记忆深处的,都并不是这地方的面貌、形态,而是发生在我与那个地方之间,那一段段似是而非真实得晃眼直击心灵的故事,它可以是漫长的十来年,也可以是一闪而过的瞬间。
这像极了漂浮在大海上逐浪而居的摆渡人,在岛屿之间,记忆游移着,我在此岸看到彼岸,念此情想起了彼景,它模糊的存在着,却又如此清晰。我想我爱,爱这些如浮屿一般生生不息长在我脑海深处的记忆,是故事用有力的笔调画出,那一个个城市,最细的轮廓,最粗的声音。
台中
二零一三年五月
陸俊文-Perry,现居厦门,滞销书作者。
图片:iamw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