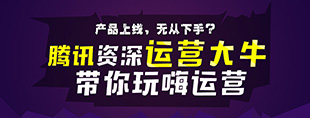(我的家乡在湘南边陲)
列车已经飞驰在它原有的轨道上,原本平静的内心因为堂哥的一个电话,变得急迫起来。似乎能从电话的那头,感受到家里热闹的气氛。
对农村而言,人生有三大事:娶妻、生娃、盖房子。我的父母早早的完成了前两项,等到他们快55岁的时候终于迎来了第三项。用我母亲的话来说,她终于完成了“任务”!是的,这个任务似乎只有我母亲一个人在完成。
我们家不过就是湘南边陲上最平凡也最普通的一家。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这个角落时,我的母亲和其他村民一样,也踏上了南下的打工之路。这笔打工挣来的血汗钱不仅抚养了2个孩子,供他们顺利读到大学,而且还盖一栋迟来的新房子。
我记忆中,最深刻的事情,莫过于我和弟弟跟随父母搬了无数次家。从村里到村外,从河边到坡地,从暂住亲戚的房子到租用学校的房子,从独居到群居……
我常听家里的亲戚说起我的祖父。说祖父是村里有名的地主,家里很多的古董珍宝,有一整栋连体的楼房。他到60多岁时娶了年轻的祖母,生下了我爷爷。而当我爷爷6岁时,祖父因为过度吸食鸦片去世了,祖母便带着爷爷改嫁到了别的村庄。从那时起,家里的大宅子、古董便慢慢的没了。
等到我能记事时候,大宅子还能依稀看到原来的模样,双天井的格局确实只有富人家才有,只是房子的另一边买给了别家的人。这所破旧破旧的大宅子,成了我母亲嫁过来的第一所房子。我的父亲母亲在这里结婚、生子,我在这里,在天井下,第一次学会了刷牙。
我印象中的这所房子永远都是黑色的。青砖瓦房因为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洗礼而显得有些破旧,墙角下会长出青苔,靠墙一侧的床要贴上报纸。时间久了,报纸会发黄,开胶的角会装满细细的砖粉末。
下雨天时,我很喜欢坐在天井高高的门槛上,看雨水打在砖瓦上,顺着低槽顺流而下,或急或缓,或重或轻,滴在了用石头有序堆砌的玉米路上,汇成小小的溪水流进了天井两侧的沟里。
爷爷去世后,家里的叔伯们开始抽签分家。我记得,我只抽中了几样家具,没有抽中大宅子,而我的二伯、小叔则抽中了。后来,二伯起新房,便拆掉了老房子。

分家后,父亲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带着一堆的家具搬到了大伯的房子里。我记得当时的房子很大,一间是瓦房,一间是低矮的平房,房子前面还有一大块晒谷场。房子临河,地基和下半层用的是火砖,上半层用黄泥土砖。
我母亲常常靠着瓦房的一侧窗户生火做饭,旁边放满了永远也烧不完的柚子树和橘子树的树干。久而久之,生火的一侧墙体变得黑乎乎了,窗户纸也变得黑乎乎了。而我的父亲,则喜欢带着我和我弟弟在床上玩。我父亲常说起一个场景,说我拿着一张试卷从学校飞奔回家,告诉他,我们幼儿园班考试了,我爸说我考了0分,我便开心的告诉他,隔壁家的晓晓也考了0分。
那会,我最爱平房的房顶,我在房顶上种了很多很多花,我常常自己搬楼梯爬上爬下。我还会自己生火烧热水,然后拿着一个大木盆,自己在门口洗澡。那次放学路过的几个大女孩看了我一眼后,说说笑笑走过去了,我总怀疑她们是在笑话我,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在大门口洗澡了。或许,从那个时候起,在大伯的房子门口,我开始知道了羞耻心。
后来,我们从大伯的房子搬到了小叔在村外的屋子,居住的空间从村子中心到了村子外围。村里人管小叔的那片居住区域叫“高头”,那边的房子叫“高头屋”,村里的房子相对成了“底下屋”。
小叔的房子是刚起的火砖屋,在一片农田的边上,门前门后都是柚子树。房子很大很大,两个房间一个堂屋,还有一个自盖的厨房。听小叔,他盖这个房子用了2万多块钱。天哪!2万多,当时我真觉得好多好多,我真是不知道我家何时才能盖房子,而我那时,还没有读小学。
或许是因为居住时间太短,关于这所房子的记忆很少,只依稀记得屋后有很多大石头,听说是我家要建新房,托人买的地基石头。
后来,我家没有起新房子,就换了另一处居住地。
小叔一家从广东打工回来了,我家又要搬家了。 这次,我们搬到了学校。
一间小小的狭长的房间,挤压两个大教室中间,那应该是老师的办公室,或者是外来的年轻老师的卧室。我很不愿意听到隔壁家的大叔说起一段往事。他常常和我描述,我妈是如何哀求校长,如何在校长面前哭哭啼啼,才得到了暂住一年的允许。
那段时光,我是幸福的。我读小学,我的家就在教室的旁边。我常常睡到大家都来上课了,才爬起来。第一节课下课后,才回家扒两口饭吃。那个时候,我母亲会用一个绳子系一把钥匙挂在我胸前。我每天上课就玩弄拿把钥匙,下课就守在家门口,不让我同学从门缝里偷看我家。
那时,家里只能放下一张床和几样简单的家具。我记得,我弟弟当时已经长到了我胳膊这里,我们家睡觉分两头,弟弟靠墙,到我母亲,到我,父亲睡在外面。我们穿插着睡觉,每天都是按这样的秩序入睡。
我的记忆便切换到了另一个场景。
我父亲和一个开便利店的人正围坐在一张四方桌子旁,我父亲在写写画画,母亲站在一侧盯着父亲手中的纸笔,而我正愉快的在旁边吃火腿肠。那时的火腿肠,真是好吃极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我家在买房子,买下了一家便利店。
便利店其实也不大,用的是水泥砖,也就一个堂屋一个房间。房间是我家的卧室。聪慧的母亲用在后门搭了一个简易的厨房。
从那时起,我家也开起了便利店,我又成了村里最幸福的小孩,我家不仅有辣条,还有两个冰箱,我可以自由的在抽屉里拿零钱……
过后不久,我家买下了马路对面的两间黄泥巴房子。那黄泥巴房子以前是用来养牛的,所以大家都叫它“牛栏屋”。
有了这牛栏屋,便有了我的青春,或者我的青春和这个牛栏屋是分不开的。也正是因为这便利店和牛栏屋,我家便安定下来了。
我还记得,我和我弟弟跟着一辆板车后面,兴奋的跳上跳下。那会,我父亲刚从村外的坡地上,拉了一车黄泥土,用来垫高牛栏屋的地板。父亲给我和弟弟每人发了一个厚木板样式的东西,像砖头,又有把柄,用来夯实黄泥土。有时候,我父亲还得那锋利的刀具铲掉墙面上的,已经凝固的干巴的牛屎。不管臭不臭,我和弟弟都捂着鼻子。
后来,父亲在牛栏屋里按了木桩,铺了木板,便成了二楼。二楼就是我真正意义上的闺房。在这里,我终于可以一个人霸占一张床,我终于可以邀请村里的小伙伴来我家住,我终于可以把从学校门口买来的明星画贴满墙面,我终于可以在枕头底下放别人送我卡片……总之,我可以用牛栏屋的二楼,我自己的空间,干各种我喜欢的事情。
在那里,我度过了近11年的时光,直到我寄宿高中学校……
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县城,二楼自然留给了我的弟弟,那也成了我弟弟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个人空间。而在此前的十几年里,他要不跟着我爸妈睡,要不跟着我堂哥睡,要不各种亲戚中轮着睡觉。等到他高二的时候,他也般到了学校里寄宿。可寒暑假回家时,他还得到我堂哥家里睡觉。
其实,二楼也并不是特别好的地方,就是一个人为隔出来的楼层,木板凹凸不平没有固定,四面墙都是漏风。到了冬天,得用各种布、箱子挡起来,把被子盖好点儿。第一次来我闺房的朋友们,几乎站不稳,到后来,她们竟然习惯了!
便利店和牛栏屋改变了我一家的生活。它不仅给我家带来了真正意义的稳定,也灌满了我和弟弟对于少年时期的记忆。 或许是因为这一次次的搬家,又或许那时正值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山沟里,我妈妈毅然决定要外出打工,以改变这种窘迫的局面。这一去便是10多年,而我也从小学四年级读到了研究生毕业。
结 尾
现在,我正在飞驰的列车上焦躁不安,我想要赶在十二点前到家,我要赶上新屋子落成的酒席。这一所新房子,对父亲母亲而言,对我一家而言,意义太重大了。
其实,我很能理解,为什么乡里人,拼命在外面打工,也要挣够回家盖房子的钱。建一所属于自己家的新房子,对于传统的农业社会而言,那不仅是财富的象征,更是一种乡情,一种对根的认同,它预示着心灵和脚下土地的凝结。